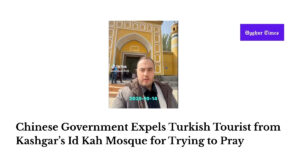伊力夏提·哈桑·阔克博热:维吾尔人重返“偷偷听歌”的时代

伊力夏提·哈桑·阔克博热的个人回忆:在数十年压迫下守护维吾尔音乐、文化与身份的挣扎
作者:伊力夏提·哈桑·阔克博热Ilshat Hassan Kokbore 2026年1月27日
近日,据多家国际媒体依据从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泄露的音频报道,在中国共产党先后查禁、没收维吾尔文书籍之后,如今又开始全面禁止维吾尔歌曲。被禁的维吾尔歌曲名单非常、非常长,其中既包括流行歌曲,也包括传统的维吾尔民歌。
事实上,维吾尔语言早已被禁止;维吾尔文化和宗教信仰早已被禁止;所有维吾尔文书籍均被查禁和没收。如今,维吾尔语歌曲再次遭遇被禁止的命运。对今天的维吾尔人而言,除了“维吾尔”这一族群标签之外,任何能够凸显维吾尔民族身份的特征,正在被一个接一个地列入这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黑名单。
我童年生活在楚鲁盖(Chuluqay)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狂风暴雪般席卷一切。那时我大约六七岁。记得一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夜,我和爷爷、奶奶正准备睡觉,忽然两位叔叔没有敲门就推门而入,夹带着风雪闯了进来。
年长的叔叔穿着的羊皮袄鼓鼓囊囊,似乎裹着什么东西。他们神秘地从羊皮袄里掏出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盒子。
我问小叔那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一个收音机,可以接收歌曲。我非常吃惊——这个东西竟然还能听歌!
爷爷立刻把屋里的旧被褥和垫子拿来,把门窗严严实实地封住。大叔把收音机的电线接到屋里昏暗灯泡的电线上。盒子开始发出咔嚓咔嚓的杂音。叔叔小心翼翼地转动旋钮搜索信号。经过漫长的沙沙声和嗡鸣声后,突然,一个维吾尔男子的声音从盒子里传了出来,仿佛是在播报新闻。他的声音低沉、有力、严肃,很像我们家门口电线杆上高音喇叭里播出的文化大革命“新人新事”。
爷爷、奶奶和两位叔叔静静地听着,仿佛完全沉浸其中。我觉得很无聊,打了个哈欠,快要睡着了。
突然,小叔兴奋地喊道:“要放歌了——要放维吾尔歌曲了!”
爷爷也激动地附和:“对,对,是帕夏·依善的歌(1),是《山溪》(Tagh Suliri)!”
爷爷、奶奶和两位叔叔沉浸在断断续续的歌声中,随后又听到了《解放的时代》(Azat Zaman)。
那歌声就像千百年来在伊犁街头传唱的民歌:时而由远及近,从模糊难辨的歌词到清晰洪亮;时而又由近及远,消失在无线电的呼啸声中。爷爷、奶奶和叔叔们仿佛忘记了严寒、忘记了一整天劳作的疲惫,也仿佛忘记了夜已深沉,最初的谨慎也渐渐消失,让帕夏·依善的歌声冲出窗外,消散在风雪之中。
帕夏·依善那富有激情、独特高音的几首维吾尔歌曲,仿佛把爷爷奶奶带回了他们短暂而幸福的青春时代——那个独立而自由的年代。
帕夏·依善唱完之后,接着是阿卜杜热依木·艾赫麦迪(2)演唱鲁特普拉·穆泰利甫(3)的《无奈》(Meylimu)以及几首喀什民歌。阿卜杜热依木对穆泰利甫悲剧诗歌的哀婉诠释,使爷爷奶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小叔开始给我讲述他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关于鲁特普拉·穆泰利甫的故事。
我在歌声中慢慢睡着了。我不知道爷爷、奶奶和叔叔们究竟听了多久。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那个叫“收音机”的盒子已经不在昨晚的窗台上了。我问爷爷,爷爷示意我小声说话,然后严肃地对我说:
“你还记得托赫提玉甫叔叔吗?村里的兽医。”
我说:“记得,爷爷。他不是被政府抓走了吗?”
爷爷点点头说:“是的。他就是因为偷偷听了和我们昨晚听的一样的歌,被带走的。”
爷爷继续对我说:“孩子,你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家有收音机,更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听了帕夏·依善和阿卜杜热依木·艾赫麦迪的歌。这些歌都是被禁止的。如果公社民兵发现了,我们全家都可能被抓走!”
我真的被吓坏了。我不想让爷爷奶奶被抓走,更不想让两位叔叔被抓走。
那台收音机在我们家待了大约一周。每天深夜,爷爷、奶奶和叔叔们都会把门窗封得严严实实,然后打开收音机听。对新闻,他们已经不像最初那样感兴趣了,他们只想听歌,尤其喜欢听帕夏·依善的伊犁民歌。
我知道爷爷和两位叔叔都喜欢弹都塔尔,也喜欢唱歌。据说爷爷年轻时还是伊犁县小有名气的都塔尔歌手。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再也不弹琴、不唱歌了。但在漫长寂静的冬夜,他喜欢教我背诵维吾尔民歌歌词,给我讲述许多维吾尔民歌的来历,也给我讲鲁特普拉的悲剧故事。
后来我回到父母身边,在哈密铁路区上汉语学校,发现家里也有一台几乎一模一样的台式收音机。起初我根本不敢碰。渐渐地,趁父母上班时,我开始偷偷打开它收听。
熟悉之后,我开始搜索各种短波电台,也找到了爷爷奶奶当年偷偷听的维吾尔语广播。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电台叫“解放电台”(Azat Radiosi),是苏联为了对付中国而开办的维吾尔语广播,节目面向东突厥斯坦,批评毛泽东时代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讲述第二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历史,并穿插播放在中国被禁的维吾尔歌手的歌曲,如帕夏·依善和阿卜杜热依木·艾赫麦迪。
当时我以为他们两人都在苏联中亚。
有一天,我正专心听“解放电台”的新闻节目,父亲提前下班回家,突然走进房间。我根本来不及关掉收音机。父亲愤怒地关掉了收音机,严厉警告我绝不能再偷偷收听被政府禁止的电台,并神情严肃地告诉我,偷听敌台会给全家带来灾难。
那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我已不再是那个无知的农村孩子,因此并未把父亲的警告当回事。
后来,毛泽东去世,政治气氛逐渐放松,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开始小心翼翼地复兴自己的文化。那些曾被禁的维吾尔民歌开始在私人聚会上出现。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帕夏·依善一直在东突厥斯坦。她因演唱某些歌曲在文革中被打倒,歌曲被禁止;而聪明的阿卜杜热依木·艾赫麦迪则早早逃离了家乡。
再后来,“四人帮”倒台,随着录音机的出现,香港和台湾的流行音乐磁带也开始秘密流传。我们这些进入青春期的年轻人开始偷偷听邓丽君、张帝等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歌曲。在这些优美旋律与深刻歌词的陪伴下,我这个用汉语参加公务员考试的维吾尔青年,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维吾尔民族复兴与自由之路。
回头看,在那个充满虚假希望和承诺的年代,我曾天真地以为,维吾尔人偷偷听敌台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偷偷听禁歌的时代也不会再回来。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短暂的宽松过后,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又一步步把东突厥斯坦重新拖回那个恐怖的禁忌时代:不能读禁书,不能听敌台,不能听禁歌。
有趣的是,90年代中期,石河子成立了经济广播电台,公开考试招聘播音员。我顺利通过考试并被录取。为培训我们,电台把我们送到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学习一周。
在那里我才知道,南昌路的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正是当年中共用来干扰苏联“解放电台”的干扰中心。也就是说,当年爷爷奶奶和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冒着生命危险收听那些悲怆动人的歌曲时,刺耳的干扰声正是从这里发出的。
“兵未出门,将先死。”东突厥斯坦的梦想和维吾尔民族的命运,就像我在石河子广播电台夭折的播音生涯一样——戏还没开场,就已走向悲剧结局。
后来,我和大多数维吾尔人一起,再次进入了偷偷听敌台的时代。这一次,敌台不再是苏联的“解放电台”,而是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广播。
起初我买了一台九十多元的香港产“德生”收音机,因为有人说听自由亚洲电台维语节目效果最好。但不久,中共的干扰越来越强,常常节目播到一半就被噪音淹没。
为了及时获取真实信息,我又咬牙买了一台两百多元、可存储多频段的德生收音机。切换频段,才能继续收听。那时,不仅汉族同事觉得不值,连家人也认为我浪费钱。
但我觉得值得。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需要知道真相。
后来,我流亡海外,来到美国。新闻自由了,但我失去了家园。在异国他乡,维吾尔语、维吾尔书籍和维吾尔歌曲,成了不可或缺的“故乡之声”。幸运的是,海外的我们至少可以自由聆听任何维吾尔歌曲,不必担心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但故土上的维吾尔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可能因为下载一首禁歌而被抓捕、判刑;可能因为唱禁歌而遭重判,例如年轻歌手阿卜拉江·阿吾提·阿尤甫(4)和穆麦提江·阿卜杜卡迪尔(5)。
更不幸的是,无论是听歌的人还是唱歌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天、哪一首歌会突然被当局定为“禁歌”。
在漫长而黑暗的冬夜,在没有维吾尔歌声、没有维吾尔民歌的死寂夜晚,在无处不在的层层监控之下,是否还有维吾尔人在偷偷听那些被禁的维吾尔歌曲?
注释:
帕夏·依善:著名维吾尔民歌手,家喻户晓
阿卜杜热依木·艾赫麦迪:逃往苏联的维吾尔音乐家
鲁特普拉·穆泰利甫:被国民党处决的维吾尔革命诗人
阿卜拉江·阿吾提·阿尤甫:被判刑的维吾尔流行歌手
穆麦提江·阿卜杜卡迪尔:被判刑的维吾尔音乐人、喜剧演员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文媒体《议报》,后由《维吾尔时报》编辑翻译并以英文发表。
伊力夏提·哈桑·阔克博热: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世界维吾尔大会中文发言人、政治分析家、前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