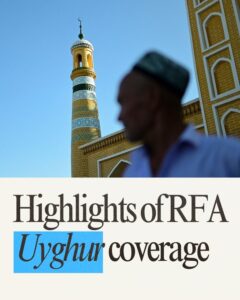21世纪的奴隶——维吾尔族人

作者:塔西尔·伊敏Tahir Imin维吾尔人
在我们自由生活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年轻男孩和女孩正被奴役在类似于历史电影中被捕获和奴役的黑非洲人一样的条件下——在严酷的身体和精神压迫与屈辱之下。
他们被与亲人、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分离,并被永远流放到无人居住的沙漠中新建的奴隶城市。
他们被扔进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中。他们被交给无情的劳动监督员,后者除了辛苦的劳动、工具和产品配额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早上六点起床,排队上厕所。除了警卫和保安人员,他们每时每刻都被分成三人一组,互相监视对方的言行。饭前,他们都举起碗,排队站在食堂前,用中文高呼:“社会主义好”,“习主席万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之后,他们穿上工作服,排队在院子里,一边节奏一致地跑步一边用中文喊“一二一”,周围是中国军队的警卫。
然后,每个人都去到指定的岗位,用工号打卡。
每个人的工作都很明确——完成苛刻的年度和月度配额,而严格的纪律是他们继续生存的唯一条件,以期望能活下来,或许能见到遥远的亲人。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或尊重,除了他们操作的机器或他们手工制作的产品。
工作场所没有说话,没有聊天,没有游戏,没有笑声,没有哭泣,没有漫步,没有打架。如果有不服从、分心、机器故障、拍照、对中国老板提高声音,甚至瞪眼——低级别者将被关进单独监禁,没有食物进行“政治学习”;高级别者将在现场由工厂军队和警卫执行刑罚。
他们的背痛,头痛,眼睛疲劳,身体疲惫不堪,没有休息。在长达14小时的辛苦劳动后,他们无声无息地享用集体晚餐,然后是2小时的电视宣传:“你们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通过劳动拯救你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只有劳动才能拯救你们。” “只有遵守规则,保卫共产党,努力工作,生产出高质量和高数量的产品,你们才能活下去。”
他们思念家人——父亲还活着吗?妹妹怎么样?女儿在哪儿流浪?如果他们能听到彼此的声音就好了。但他们不能打电话。
他们的精神疲惫,他们哭泣,他们的舌头被检查,他们的头被洗,有时被殴打。他们的日子在恐惧和殴打中度过。他们对世界和生活失去了所有希望。年轻人听到殴打和痛苦的哭声。每个奴隶工人只能想象殴打和鞭打的恐怖,直到他们自己被剥光衣服并被打进“纪律”。有时在夜晚,被中国老板挑中的女奴工人被强行剥光衣服供其性娱乐。他们宁愿死也不愿受这种屈辱。有些确实死了。随后,他们被更加严格地监视,甚至连自杀的机会都被剥夺。
他们与外界的隔离是巨大的。他们只能通过渐渐消退但仍然存在的记忆来想象生活和外界——他们曾经的生活,家园,邻居,熟悉的面孔和他们的故事,衣服,食物,书籍,音乐,他们参观过的城市。
对他们来说,世界是拥挤的宿舍,工厂建筑,害怕的面孔,恐怖的鞭打声。
“如果我能在吃一碗类似的拉条子面条时死去就好了!我还能不能再尝到东库鲁克的那碗酸辣拉条子?”来自阿克苏的43岁的加里普说,他被奴役在吉林的一家中国工厂。
“我的女儿在上小学,她现在应该是个大姑娘了。她会想我吗?她一定会,一定会哭的。”来自和田的36岁的古尔加马尔说,她被关押在广东的一家工厂。
“已经四年没有联系我的妻子和两个小孩了。他们在哪里,他们还活着吗?我为他们而活,我会想办法出去。”来自伊宁的卡尔穆拉特说,他被关押在塔克拉玛干新建的奴隶城市。
“我的父母在营地里去世了,我的哥哥和表弟因为有亲戚在土耳其被判了15年监禁。他们有小孩子。为了他们,我会坚强!”来自乌鲁木齐的阿尔祖古尔说,她被关押在奴隶城市。
“我没有力量了,我累了,我没有希望了,这些不是人,他们毁了我的身体,摧毁了我的自尊,夺走了我的一切。与其在这样的恐惧和畏惧中活着,不如我去死。我会找到办法自杀的,我会去激怒那个门卫,他会开枪打我——那是最和平的死法!”来自喀什的玛米特江说。
这些是21世纪被遗忘的奴隶,被不人道的中国政权和无情的中国公司通过对人类劳动的极端剥削、物质贪婪和政治议程在工业规模上奴役的无声受害者。
他们是维吾尔奴隶,是21世纪最恐怖的人类精神中潜伏的最恐怖思想所奴役的最大规模现代人类奴役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