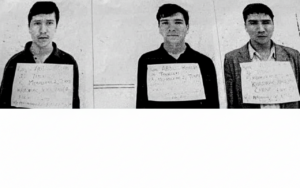专访:古孜拉·阿瓦尔汗Gulzira Auelhan

您好古孜拉女士,感谢您接受我们报社的采访。
问:在集中营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答:早上警察和老师从宿舍带到学习班,警察带到课堂。课堂里面唱歌,吃饭之前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课的内容就是学习习近平思想,党的政策,一天要上14个小时政治课,期间有两次去洗手间的时间,如果期间晚回来了,警察会拿电棒打你的头,每次上课过程中还要写一些感想,忏悔录,感谢党的政策,未来的计划想法,每篇文章要四页左右。因为中文不怎么好,要用哈萨克语写,然后老师翻译,每个学生会朗读他们的文章。
问: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用维吾尔语唱的吗,还是汉语?
答:必须用中文唱歌,如果唱错的话,他们会被骂被训,自我介绍必须用中文。集中营里面也有法论功学员,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会中文的用中文写,会维吾尔语的用维吾尔语写忏悔录
问:一堂课大概多少人?
答:他们最后一次是最多的一次68个人,一般在40-50人数会变动,有些人会转去其他监狱或者学习中心,宿舍最少住12人,最多是66个人一个大宿舍。
问:您提到学习中心里有法论功学员,他们是汉族人吗还是其他族裔,您怎么知道他们是法论功学员?
答:我2017年7月19日被抓到北山坡的一个监狱,9月份转到其他再教育中心,到了新的宿舍,待了两天,里面有8个回族女士,9个汉族女士,和她们交流以后,里面有一个叫马修瑞的女士,是班长会哈萨克语,她们是因为法论功被抓的,两天以后被转到其他牢房,里面那些人对我帮助很多,刚来的时候帮我垫床铺,牢房里面除了有维吾尔族,还有法论功学员,回族,柯尔克孜族,来自土耳其的奶奶
问:来自土耳其的奶奶,是土耳其人,还是土耳其族被抓到集中营里去的?
答:土耳其女士,她的母亲是维吾尔人,1940年代逃到土耳其避难的,嫁给一个土耳其男士,母亲希望看看她的家乡,然后她到新疆就被抓了,10-15天后被放了。她母亲的情况了解的不是很多,在监狱里不敢交流太多,也就大概了解了一些。监狱里有个哈萨克女生,她是留学生,她在北京上学,20天假期间回到新疆被抓了。我问她为什么被抓,她回答说手机里有扣押软件,有VPN上课查资料用的。还有一个上海的回族女孩儿,也是类似的情况被抓。
问:也就是说中国的公安或者警察他们有手段知道每个人手机里是不是下载了软件,而且不需要通过本人同意,只要知道了就会抓人是吗?
答:物理上查拿他们手机查,新疆有要求,外人来你家的时候,必须要向公安部通报,家里来人,要求去公安局,到了公安局发现手机里有VPN就把人扣了下来。她们说好不容易从学校弄来证明,然后才被释放了,之后有没有回北京和上海就不知道了。
另外在再教育中心有个叫周树人的女士,据说她因为想盖大一点的房子,儿子要结婚,当地政府认为这种行为是提意见,然后被关起来了。这个人下肢瘫痪,只能坐轮椅。我们两人上下铺,我就帮她洗衣服帮助她,我们之间也有了好的感情。还给她安了一个法论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问:拘押期间您是靠什么样的力量坚持下来的,同时在被迫的做很多事?
答:刚开始进再教育中心时恐惧过,想念过家人和亲戚。在此期间被打过针,可能药物的影响,变得像僵尸人,只关注什么时候吃饭,完全没有思想的念头像机器一样。看到这些惨无人道的现象,我也绝望过,也有绝望时刻。但因为我的老公在哈萨克斯坦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不断努力,我被释放了。回到哈萨克斯坦和来到美国,但我依然在这种恐惧之中。因为之前的室友像家人一样,出狱前我和那些室友保证过,如果我能到国外会帮助大家出狱。所以我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希望有一天那些室友们也能被释放。包括法论功学员,维吾尔人等等。我们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些遭遇。
问:您刚刚提到打针,是强迫的吗,每个人进去都要打针吗?
答:第一次进再教育中心的时候,我们22个女生被带到妇女儿童医院,体检过程中被裸体检查,也检查了下体。我们回到再教育中心之后,负责人说三个月之后要打一个预防感冒的针,因为人很多容易传染,费用是250元,我不知道这个针是我们家人付的,还是政府付的。如果不打这个针,我们会被转到其他再教育中心。所以被迫的打了这个针,这个针六个月以后会有效果。但打完针以后女生就停经了,一些女士记忆力下降。
问:就您所知这个针只是针对女性吗?
答:再教育中心是女性囚犯,谈话的时候也有男性警察谈话。被关15个月期间,19次被谈话了,大部分是男性警察。夜间巡逻和上铐的警察也是男性的。
问:问一个题外话,您知不知道,维吾尔族文化里面是不是男性和女性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答:在伊宁县有很多哈萨克人,监狱时见过一些维吾尔人,对维吾尔的习俗不是很熟悉
问:您的先生在哈萨克斯坦和一些国际组织帮助救援您,您当时在监狱时知道这个事情吗,还是出狱后才知道外界关注您?
答: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补充一下,每天卫生间厕纸需要清理,厕纸是由古兰经其中的页纸制作而成,羞辱我们。当时在监狱的时候,只是关注学习,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能和家人报平安。被释放以后,可以用微信和我老公联系。我老公说让我赶紧办护照出国,我老公让我不要多管闲事,担心又被送回再教育中心,安静的带着。6月26日,县委书记杨兴平带着一个翻译,告知我可以回哈萨克斯坦。但我需要编一个理由,说我护照丢了,所以才待了15个月。要么说自己病重,待了15个月。我问那些老师,弄一份丢失护照的证明,又去找医院开一个病重的证明,医院也开不了。一直到到了哈萨克斯坦才知道外界的帮助。
问:出狱后到现在也有了一段时间了,这些经历您觉得最让您难忘的是什么? 以及在再教育中心期间,对您的文化和自我认知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答:2017年国家安全局告知我被关的原因是因为我去过哈萨克斯坦,哈色克斯坦是涉及恐怖主义的二十几个和国家之一。第二个是,在被关押期间,老师们强调要和汉族人同吃,同工,通婚,我担心这种强烈的同化政策。这样会消灭宗教,消灭语言。少数民族的母语应该受国际法律保护的。所以到这边以后接受很多采访,但因此我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
问:您提及2017国家安全局告知您原因,具体是哪个地区的国安局,哪一级的国安局?
答:是伊宁县的当地国保,是刀廊牧场四大队的。2017年我的大女儿也被关了,是因为护照过期。我一直到我出来以后才和大女儿见面的。2017年1月我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的时候,护照被扣了。边境人员告知我,当地的公安要把我带走审讯。当地的警方凌晨两点带我去审讯,审讯完以后我被放了。我说我想见我父亲。警察告知除非参加15天的学习才可以见。
问:最终您见到您父亲了吗?
答:每次去我父亲那里都需要申请。2018年的10月9日被放了以后,我也想去见我父亲。但据说我被举报,我一直被人跟踪。2018年10月14-17日,宋书记逼迫我签黑工厂合同,宋书记是刀郎农场第四大队负责人。他把我安排到一个纺织工厂,要求我工作三个月,每月600人民币。三个月之后才自由,才可以回哈国。期间偶尔被带回家里。后来才知道,我先生在国外为我申冤。我猜测是这个原因。三个月以后原本还要求我继续工作,但因为海外的追踪和报道,我才被释放的。
问:这三个月您做什么呢?
答:织手套,在伊宁县加纺纺织厂
问:在纺织厂期间,吃住有没有人管,条件如何?
答:期间属于管制状态,北京时间凌晨4点有公交车从宿舍楼带到三公里以外的工厂,到了之后有几分钟的吃饭时间,之后要用一个小时学习党的政策。我有个便利,可以自由用卫生间。不像在学习班有限制。我们还可以用手机,厂里面有WIFI。每周六我们可以回家,住在家里。每周日公交从家里带走送回宿舍楼。宿舍里面也有摄像头,三四个女孩在一个宿舍里。
问:您对中国是个什么概念,什么时候听到中国这个词的,中国对您是个什么概念,您是怎样认知这个概念的?
答:我们从小就生活在新疆,也没有太多国家的概念。2017被关押期间,监狱老师说这种政策三年前主要针对政府人员,老师,警察进行再教育的政策并积极灌输。2017年4月11日向社会人员推行直到2020年全国推广,2030年这种再教育的模式向其他国家推广,和周边国家合作。2050这种中国模式会推广到全世界。再教育营里不能只叫新疆,要叫中国新疆。一直宣传会在全世界推广中文,推广他们的产品。这种政策是辅助一带一路政策的。这种叫法有点变化,以前是一种地域概念,现在变成一种战略推广。变成一种帝国主义的印象。
问:很多国际人权支持者将“新疆”这个地区称为东土耳其斯坦,有些称东突厥斯坦,有些称维吾尔斯坦,有些称为准噶里亚,您作为一个哈萨克斯坦族裔,您认为这些称为是否准确,或者有没有一个专用名词来描述这一地区?
答:我尊重各自人员他们的看法,他们怎么称呼是各人的意愿。做一个普通人,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没有要求过独立。入境的时候因为去过哈萨克斯坦被关了18个月。我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诉求。我出生在哈萨克,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学过维吾尔语,不会维吾尔语也不会中文。地理上的称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想参与太多的政治偏向,只想多关注人权。
我尊重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维吾尔族人,各族当中有好人有坏人。中国有56个民族,民族是不可能分好坏的。邓小平时期有好点的民族政策。爷爷告诉我他当年11岁的时候,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烧过古兰经。现在也在将古兰经当厕纸,历史在重演。但是我不会把仇恨加诸于汉族人身上。这是一个独裁政策,之前是毛泽东的独裁,现在是习近平的独裁。我希望我们应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加强合作。
三区地区是昔日游牧民族哈萨克人自古以来的领地,三区革命英雄 Ospan Batyr 的陵墓至今被中共政府监督,以防有人膜拜陵墓。1943年哈萨克诗人Tangjaryk Joldy 在盛世才的国民党监狱被折磨致死,我在2017年也重新“体会”了诗人的遭遇,历史在重演。
问:您到美国以后,您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有人权方面的工作吗,可以介绍一下吗?
答:傅希秋先生帮助我来到美国,我想感谢傅希秋先生和ChinaAid,台湾的朋友。傅希秋先生的功劳很大,他也一直在帮助宗教迫害人士包括法论功学员和基督徒。来到美国和在哈国的时候也一直接受采访。唯一的问题是主要问题,不懂中文和英文。担心翻译方面出差错。我也做过证,也为有关强迫劳动的事情做过证。一直为推动强迫劳动法案努力,也见过议员。在美国商场也偶尔看到过中国来的产品,看到这些产品会心疼。我担心这些产品是不是也来自强迫劳动工厂和类似的工厂,是不是也来自其他人的泪水。我希望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不能只为经济利益为主,应该以人权为重。我希望所有人被释放。我计划继续拯救其他人,继续发声接受媒体采访。我想出书,做一些纪录片,把这些经历的过程留下来。让后人知道。在再教育中心期间,那些老师们也说过中国政府会用这种软实力占领世界经济市场。在中国织一双手套要十分钱,在国外要卖250元人民币。应该要出台更严厉的政策来制裁中国的这些产品。希望关闭这些强迫劳动工厂和不人道监狱。希望这些人能被释放,不论种族和地域。
问:再教育营的老师们都是汉族人吗?
答:里面有汉族老师,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大领导都是汉族人。
答:我有些问题想不通,我被消失的这两年间,没有法律的裁决书,所以我不是犯人,我希望用法律的手段继续诉讼,想要赔偿,也为其他人伸冤。我有点想不明白,有些维吾尔和其他人在海外还在使用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合作。在美国我没有买过中国产品,我那个时候一个月才领到250元人民币每天工作14个小时,因为达不到标准这有这点工资。那些人都在死亡恐惧的边缘,如果有异议要么就被关进监狱,要么被强迫劳动。所以我希望继续为他们发声。
我在美国有三种感受,第一恐惧, 我来美国之前以为美国没有中国产品,但到了之后发现遍地都是中国的廉价货物,我担心这些货物来自强迫劳动,需要继续制裁中国产品。我还了解到大家都用Temu软件订购商品,但这是中国制造的软件,用类似的中国软件对于隐私有风险,如 Tiktok。最后,我发现到美国的新疆人也倾向于使用中国货,这是不好的趋势。
古孜拉女士想向读者说的
我一直在参加声援维吾尔人或者中国人的活动中每次都会被边缘化。要么被当成维吾尔人,要么被迫站在要求站在支持独立的立场上。我希望主要关注人权方面的问题,以哈萨克族裔这个民族身份。至今,在新疆汉族人可以出国,但哈萨克族依然不可以会受到限制。我在被关押期间会被打,被屈辱,被折磨了两年期间。我会要求精神赔偿。这期间警察打我的头部,警察和我说他们不能留酷刑的证据。所以只能用电棒打女性的头发。我的肾有问题,月经方面也有问题,一直在头疼。我希望有个公道,会一直坚持。
我的恩人和知心朋友们都是国际媒体记者们,包括,BBC, ABC, 半岛电视台还有其他媒体记者们,你们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永远站在正义一边,我也会继续我的奋斗,我愿意随时随地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非常尊重台湾人,China AID,他们帮助我们很多,为我们找律师找法律途径,我支持台湾人,我在监狱里看过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也不会保持沉默。
在一些视频里,可以看到我为强迫劳动作证2个小时之后,在议会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对于揭露强迫劳动事件当中也有一大部分哈萨克证人们的功劳,但是在新闻和法律上只注重讲维吾尔,还有维吾尔大屠杀 Uyghur Genocide,而且有些篇报道里把我说成是维吾尔人。我们在一些法案通过之前在议会门前集会,但是那些报道里只说维吾尔强迫劳动,之前热比亚时期也没有强迫劳动的新闻证据,但是最近在我的作证下,发布了大量有关强迫劳动的文章,也通过了维吾尔法案,但是哈萨克人在揭露强迫劳动和再教育营的过程中贡献很大,但不会被提及,而且这篇报道把我说成了维吾尔人,我对此很生气,我希望媒体应该公平公正报道,而不是片面的报道,谢谢。
最后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本此采访经过古孜拉女士的审阅;本次采访通过法国的Meiirbek帮助翻译,在此也表示感谢)